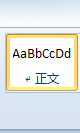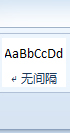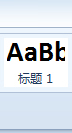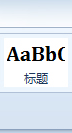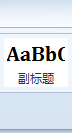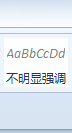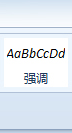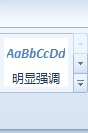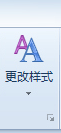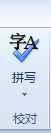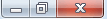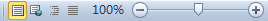到%确定
◆关于其他关系与习惯的效果的论述
无论前述论证有着怎样的说服力,我们绝不可以自我满足,必须多方面对这个题目加以研究,这有利于提出一些新的观点,来解释和证明那些奇特、基本的原则。对于接受所有新的假设时所表现出的怀疑与犹豫,原本应该是哲学家们值得夸耀的一种心情,而且对真理的考察也是十分必要的,所以我们对这种心灵应该感到满足,它还让我们来拿出令他们满意的全部论证,让妨碍他们推理的每一种反驳彻底消失。
我多次强调过,除了原因与结果之外,相似关系与相近关系,同样可以被看做思想的结合原则,因为它们可以把想象从一个观念带到另一个观念。我还说过,当这些关系中的某一种所产生联系的两个对象中的某一个,于记忆中或者感官前直接呈现出来的时候,心灵不但借着联结原则被转移到了与其相关联的对象,而且还借这一原则与现前印象的联合作用,用一种另外的强力与活力对其相关的对象进行想象。我之所以说这些是因为,我想要利用类比推理来证实我们的因果关系的判断过程。但反对我的恰恰有可能就是这个论证,也许它不能成为我们假设的证明,反倒会成为一种反驳观点。因为也许有人会说,假如假设的每个部分都是准确无误的,即:如果这三种关系都来自相同的一些原则;如果它们在活跃与加强我们的观念上都起着相同的作用;如果信念不过是对观念的一个有力且活泼的想象;那么我们的结论就该是:我们不但能够从因果关系得来那种心理作用(信念),接近与相似关系也能得出来。但是,既然我们凭借着我们的经验发现了信念仅仅起源于因果关系,倘若两个对象不是由这种关系联结着,那么从一个对象推至另一个对象的过程也就不会有了。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说,那种推理中的某种错误导致我们陷入了这些困难当中。
这便是反驳了。接下来我们要考究它的解决办法。显而易见,一切出现在记忆当中,而且通过一种与现前印象的活泼性来使心灵得到刺激的类似东西,一定会在心灵的全部作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并且非常容易就把自己与想象的单纯虚构加以辨别。我们让这些印象以及记忆观念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系统,其中包含了我们所记得的原来呈现在感官之前或者内在知觉的所有东西;系统中的每个特殊项目与现前印象进行结合,我们把它叫做一个实在物。然而,心灵并不在这里停靠。这是因为,心灵发现习惯把这个知觉系统(即因果关系)与另外的知觉系统联系在了一起,因而心灵就进一步去思索那个知觉系统中的某些观念;同时还因为它感到,它在某种意义上理所应当地被决定了要对这些特殊观念进行观察,而且决定它的这一行为的那种习惯以及关系不能有任何变化,于是它就把它们变成了另外一个新的系统,并严格地把它们叫做实在物。第一个系统包括的是记忆与感官的对象,而第二个系统则包括的是判断的对象。
后一个原则让我们了解了因时地远隔而使感官与记忆所无法达到的那些存在物,并用这些存在物填充世界。利用这个原则,我能够运用自己的想象描绘宇宙,还可以将我的注意力任意置于宇宙的某一部分上。下面是我形成的一个与罗马有关的观念;即使我从未与罗马蒙面,也不记得罗马是谁,但罗马却与我和旅行家、历史家们的谈话以及他们的著述中得出的那些印象有联系。于是我就将这个罗马观念置于我称做的地球的这个对象的观念的某个地方,并且我还在这个观念上加了一个特殊的风俗、政府和宗教的概念上去。然后我再次回想以前,思考它最初得以建立时的场景,充满了革命、成功以及不幸。我所相信的这些以及其他事物都不过是一些观念而已,不过它们通过习惯和因果关系所产生的强力与固定秩序,不同于完全包含于想象产物的其他观念。
就接近与相似关系的影响来说,如果二者的对象包含于这个实在物的系统之中,那么这两种关系必然是有助于因果关系的,并且会投入更大的力量来灌注那些与想象相关的观念。现在,我便对这一内容进行一番充分的详述。与此同时,我还要更加深入地说明我的看法,即使有些时候相关的对象不过是一种虚构的东西,这种关系也能使那个观念活跃起来,并且扩大它的影响范围。如果一个诗人借美丽的花园或者草地的景色来激发自己的想象,那么对于极乐国土,他便更能构建一幅生动活泼的写景画面了;就像在另外的某个时候他也能通过自身的想象身处神话境地中,从而用假设的相近关系来激发他的想象一样。
然而我虽无法完全摆脱相似关系与相近关系利用这种方法作用于想象,不过我们能够发现,当只有它们其中的某一个出现时,它们的影响力是十分微弱而且是不确定的。就像我们要利用因果关系来促使我们认同那些真实的存在,而且,我们要用这种信念为这方面的其他关系加强力量。因为当一个印象呈现出来的时候,我们不仅虚构其他的对象,还会任凭自己的喜好而促使那个对象跟那个印象形成一种特别的关系,不过对心灵来说,这个对象造成的影响是很轻微的;并且当这个印象再次出现时,也没有什么用来决定我将同一对象置于对它的同一关系之中的充足理由。心灵也不必虚构任何类似的或接近的对象;如果虚构了这类对象,它不一定一直限于这个对象的范围,而绝对不允许存在丝毫的不同或者改变。我承认,这样的虚构的确极少有那些理性充当它的基础,所以除单纯的任性以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使心灵产生这样的虚构;而且那个任性原则是变化着的而且是不确定的,因此它的作用不会产生多大程度的强力与恒常性。为心灵所预见的那种变化,从最初的瞬间起就意识到它活动的散漫性,无法牢牢掌控它的对象。我们在单一的例子中能够轻易地发现这个缺点。然而由于经验和观察的再次提高,这时我们就能够对我们想起的各个例子加以比较,然后确立一条通则:对于凭借虚构的类似与相近关系而在想象中所发生的那些浮光掠影,我们不能有丝毫的信任。
因果关系却具备了与此相反的全部优势。它呈现出来的对象是固定不变的。记忆的印象绝对不可能发生丝毫重大的变化;总有一个准确的观念随每个印象而来,这个观念在想象中发生,进而变成一种坚定而实在、固定不变的东西。思想毫无选择或者犹豫的机会可言,永远被支配着从印象到观念,然后由特定印象转移到特定观念。
然而我不仅仅满足于消除这种反驳,我还要力求通过这个反驳找出能够说明现在这个学说的论据。相似关系与相近关系的作用比在因果关系中获得的作用要小很多,可它们还是有某种作用,可以加强任何概念的活泼性与任何观点的信念。假如在我们已经研究过的例子以外的其他新的例子当中对我们这一说法加以证明,那么我们所提倡的信念只是关系着现前印象的一个较为生动的观念的那种说法,就可以获得一个极其关键的论证。
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相近关系:基督教徒与回教徒说过,那些朝拜过麦加与圣地的香客,较未曾获得这种优势的人来说,此后都变成了更为虔诚与热忱的信徒。要是一个人的记忆能力可以带给他沙漠、红海、耶路撒冷以及加利利的生动意象,他就不会再对摩西或福音书著者所记录的那些神奇事件产生任何怀疑。这里的生动观念自然地转移到那些被假设成因相近关系而与它们相关的事实上,并且由于想象活泼性的增强而使那种信念同样有所增加。这些对于河流与田野的记忆对一般人的影响,和新的论证所带来的影响是一样的,而且通常情况下产生的原因也是一样的。
我们也能够用同一种方式来观察相似关系。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我们从某个现前对象推得的不在我们面前的它的原因或者结果的那一推论,绝对不是建立在从那个对象自身所得到的那些性质上;换言之,除借助经验外,我们都不能判断出任何现象产生的结果将会如何,以及在它以前发生过什么。即使这一点如此显而易见,看似不用进行任何证明,可有的哲学家反而觉得,运动的传达的原因也很明显,从而一个具有理性的人在不用借助于以前的任何观察的情况下,能够凭着一个物体的撞击推断另外一个物体的运动。很容易发现,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因为如果仅从物体、撞击和运动这三种观念我们就能够得到一个推论,那么它就相当于一个理证,并且一定涵摄所有反面假设的绝对不可能性,因此,除运动的传达以外的所有其他结果都将涵摄着一种形式矛盾,它既无法存在,也不可能被想象。但我们立刻就能让自己相信这种相对立的说法,因为我们能够明确而一致地对一个物体进向另外一个物体进行想象,想象二者在接触时便立刻停止;或者想象它依原路返回,想象它的消失,想象它的圆形的、椭圆形的运动;简言之就是,想象我们能假设它遇到的其他若干变化。所有这些假设全是自然而一致的;而我所想象运动的传达较那些假设,以及其他所有自然结果要更加自然而一致,其原因就在于根据原因和结果的这种相似关系;这种关系与经验结合在一起,同时也将这些对象结合得相当紧密,以致在我们想象中它们是完全无法分开的。所以说,相似关系有着和经验平行的或者相同的影响。既然经验的唯一直接效果是联结我们的观念,于是得出的结果便是:按照我的假设,所有信念都形成于观念的联结。
为致力于光学著作的人们所公认的,无论眼睛在什么时候都能观察到数量相同的物理点。对于一个站在山顶上的人来说,与处于异常狭窄的房间或庭院中的那些人相比,在他感官前所显现出来的映像也不会有大小上的变化。之所以能够推论出对象的大与小,不过是他借鉴了经验的结果,并且利用了映像的部分特殊性质;再者,他将这种判断的推论与感觉混淆在一起类似于某些场合下经常所发生的情况,然而,很明显的是,这里的判断的推论较我们一般推理的所有情况都更为生动;假如当一个人站在矗立着的海角的最高处,对比他单单仅能听到海水的呼啸声,前者可以让他依据从自己的眼中所接受的映像,对于大海形成一个更加活跃的概念。欣赏了海洋的宏伟景象之后,他感到的是一种无比亲切的愉悦之情;这说明他可以形成一个比较生动的观念;此外,他还混淆了他的判断与感觉,这是生动的观念的另一个证明。在两种情况中,既然它们的推断都是那么确凿而直接的,我们的想象在前一种情况中的活泼性之所以会更强烈,只能归属于以下情况:在借助视觉对事物加以推断的时候,存在于映像与我们所推论的对象之间,除习惯性的结合之外,还存在着一种相似关系;这就使那种关系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加强,并通过一种比较容易而自然的活动方式将印象的活泼性传递给相关的观念。
在人性中,一般情况下所说的轻信(也就是说过分轻易地相信别人提出的证据)是最为普遍和显著的,用相似关系的影响也能够很自然地说明这个弱点。当我们凭借人们提供的证据来接受某项事实时,我们对其信念的根源,较我们从因至果、从果至因推断出根源没有差别;而且也正是我们有了对于支配人性原则的经验,所以才对人的忠实可靠有了一种信任。即使经验的确是这一方面的一个真正的标准,当然,它还是一切其他判断的真正的标准,但我们也不能完全凭这个标准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我们通常都会相信报道里所说的,哪怕是与幽灵、妖术、神异有关的报道,即使这方面内容的报道有违平日的经验和观察。他人的言辞与言谈等和他们心里的一些观念紧密相连,并且和它们所表象的对象与事实有某种关联。后一种联系往往得到过分的关注,强迫我们对经验所无法证实的事情加以认可。这种情况只能在观念与事实之间的相似关系中出现。其他结果只能间接地把它们的原因提出来,而人的见证却可以直接找到它的原因,既被当做结果的同时,又当做一个意象。难怪我们如此粗略地用它推断出结论并对它进行判断时,比起判断其他题材,反而不受经验的指导。
既然相似关系在结合了因果关系后,有利于我们的推理,那么要是没有了相似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也就完全将我们的推理瓦解了。对于这种情况,最具说服力的例证莫过于人们对来世的惯常的忽视与愚蠢,他们对此方面表示出始终不信的态度,就像在其他方面所表现出的盲目相信一样。看到如此多的人对于来世状态那么漫不经心,这种现象的确让好学的人倍感惊讶,令虔诚的人更是甚为惋惜;许多优秀的神学家坚持说,即使一般人没有可遵循的无神论方面的理论原则,但他们的心里却是无神论者,而且也没有什么关于所谓灵魂永生的信念,这话的确有道理。我们首先回想一下神学家们对永生的重要性展示出的滔滔不绝的辩才,同时还要反省一下在永生这一方面,即便我们善于大肆渲染,也远远不能与这个题目相匹配。接着,我们再从其他方面考察一下对于此事人们究竟怀着一种怎样的泰然自若。所以我要问的是,这些人对他们所受的教导,以及自称对这个道理的肯定真的就没有怀疑吗?显然,给出的答案是否定的。既然信念是从习惯的某种心理作用而来,难怪没有了相似关系,就摧毁了由习惯建立起来的那些作用,并使观念的强力得到了一定的减弱,就像习惯原则使它的强力得以增强一样,来世状态是我们力不能及的,对于人的身体被分解后,我们又将处于何种生存方式的观念又是如此含混不清,所以无论我们创立出的理由多么有力,也无论其受到了教育多么大的协助,对于想象迟钝的人来说,这种困难是永远难以磨灭的,或者也不能对观念提供强大的力量和权威。在我看来,这种不信现象的出现,原因在于来世状态与现世生活之间缺乏相似关系,而不是由于来世太久远。所以我们对来世的观念只能是模糊不清的。我觉察到,不论哪个地方的人,对于自己身后有可能发生的与现世有关的事情表现出极大的关心;比如对于自己身后的名誉、亲朋好友、国家等,无论任何时候都表现出极大的热忱和关心。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缺少了相似关系,信念就被彻底摧毁掉了,对于这个题目的重要性,除了极少的人会经过一番冷静而深刻地反省,并刻意地通过反复记忆的方法,把有关说明来世状态的论证铭记于心,很少有人能用真实确凿的判断(例如,依照由旅行家与历史家们的证据所推得的这种判断)评价灵魂是否可以真的永生。当人们对存在于现世与来世中的快乐与悲伤、奖赏与惩罚进行比较的时候,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即便事情与他们自己并无关系,同时也不存在干扰其判断的任何激烈的情感。基督教世界里的天主教徒不愧为那个最为热忱的教派,但你会发现,教派中那些较为开通、明事理的人极少会谴责圣巴多罗买节的屠杀与火药阴谋的暴虐与残忍,虽然这种阴谋和暴行的策划执行对象是他们要坚决判处永远且无限惩罚的人们。要为前后内容产生的矛盾加以解释,我们只有一句话:对于他们来世的状态,他们真的不能确定;这个前后矛盾恰恰是这种不信任的最好证明。
我们还能再补充一点:我们乐于接受由宗教方面带来的恐怖,那些能够带来最凄惨、最压抑情感的人便是最受人们欢迎的讲道者了。我们一般都能够深深体会恐怖题材的真实性,因此,恐惧和恐怖是一件最令人不愉快的事情了;恐怕只有在戏剧表演以及宗教进道中的这些情感,才能使我们快乐起来。对于后面的这些情况,想象悠然地自我陶醉于恐怖观念;而情感也因为对于题材信念的不足而倍感轻松,所以最后的愉快经历也就只有活跃心灵、集中注意力了。
如果我们仔细回想一下其他各种关系与习惯产生的效果,将能更进一步地证实现在的这个假设。要想明白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考虑到的是:在我看来,那种能够产生所有信念与推理的习惯,可以利用两种不一样的方式对心灵起作用,从而使一个观念得以加强。因为,假如我们在以前的所有经验中,发现两个对象总是粘在一起,那么显而易见,当其中的某一个对象出现在一个印象中时,我们往往就会因习惯的原因,很容易地把注意力转移到与之相随的那个对象的观念上;而且一定会根据当前的印象以及顺利、一致的推移,对那个观念保持一种较想象中的那些松散、飘荡的意象更加有力、更加生动的想象。其次,我们还能假设,纯粹的一个观念,不存在任何这类特别的、甚至是人为的准备,也时常在心灵中出现;那么,这个观念势必会逐步汲取一种便捷和力量,同时因为它有一种可以牢牢把握心灵的能力,因而很容易地进入心灵,所以它是不同于那些新的、不常见的观念的。这也便是这两种习惯的唯一仅有的相同之处:如果两者对于判断所产生的影响完全是类似和相称的,那么我们当然能够下结论,之前为解释那个官能所作的论述,已经是令人满意的了。当我们对教育的本性与效果进行考究时,我们还有必要怀疑这两种习惯给判断所带来的一致影响吗?
自婴儿时起我们已经习惯了的、对事物的那些观点与概念,全都是难以磨灭的,就算我们用尽经验与理性的所有力量,也难以将其除掉;对这种习惯所产生的影响而言,不仅逐渐靠近于由于因果的恒常而无法分离的结合所形成的习惯,甚至在很多场合下超过了那种习惯。我们在这里不应该仅仅满足于观念活泼性产生了信念这一论说,我们还应该提出,它们两者实际上是同一的。每一观念的不断重复,都能将它固定在想象当中;当然,这种重复本身是不可能出现任何信念,假如那种心理作用(即信念)能够根据我们本性的最初结构,仅仅依附在我们对观念进行的比较与推理上。习惯有时候能够使我们在对一些观念进行比较时犯下某些错误。以上便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它产生的最大效果。但事实上它无法取代那种比较,也无法形成归属于那一原则的心理作用。
某人的一条腿或一个肩膀被切除了之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然会试图运用它们。许多人死后,一整家的人,特别是他的仆役们经常会说,他们不相信他已经不在人世,还一直想象他依然停留于他常在的那间房子或是其他某个地方。在某些交谈当中,在提及某一名声显赫的人物时,经常会听到一个与他素不相识的人说:“虽然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但是在我的想象中,我仿佛曾经见过他,并且是久仰他的大名了。”这些例子讲述的是同一道理。
假如我们以恰当的观点去研究运用教育所进行的这个论证过程,会使它有说服力;而要想它的说服力更强的是:它是确立在一切地方所能够触及的最为一般的现象之上。在经过一番考察以后,相信我们能够发觉,在人类中盛行传播的那些观点,它们大多数都是来自教育,并且那么漫无目的地被信从的原则超过了那些来自实验以及抽象推理的原则。喜欢说谎的人因为谎话不断,会最终记住那些谎话;当然,判断,不如说是想象,也能够以相同的方法让观念留下更加强烈的印象,还要用清楚的程度进行想象,甚至对于那些观念来说,能够和记忆、感官或理性所呈现给我们的那些观念相同的方式对心灵发挥作用。因为教育并非是一种自然的原因,而是一种人为的原因,但通常教育的准则又有悖于理性,以致异时异地还会有自相矛盾的情况出现,因此哲学家们一直都在否认这种原因;实际上,它和我们借因果所作的推理一样,基本上都是建立在相同的习惯以及重复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