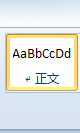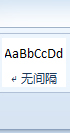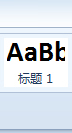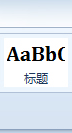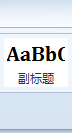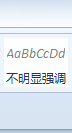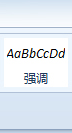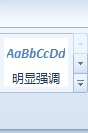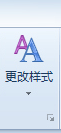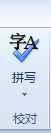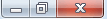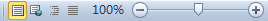到%确定
3
不管是在基督那支离破碎、不明确的教义里,还是在圣保罗对基督教的神学和社会意涵做出的更加有力和成体系的解释中,教会明显都应该是一体的和普世的。不过保罗的普世主义(保罗才是大公教会真正的创建者)并不特别依赖于某一种特定的关于未来应该如何的政治观点。基督教的“新人”是真正的世界主义者。信徒可以居住在任何地方,受任何类型统治者的支配。把他和同伴们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共同的习俗或法律,而是在基督里的团契生活。基督教将斯多葛派的世界大同梦想(全世界只有一种秩序)精神化,或者说具象化了。在新秩序下,人为造成的差异将会因为所有人对圣子(他也是人之子)共同的爱而消失。这个“重生的人”,圣保罗告诉小亚细亚西部里卡斯河河边歌罗西城的居民:
在此并不分希利尼人、犹太人、受割礼的、未受割礼的、化外人、西古提人、为奴的、自主的。惟有基督是包括一切、又住在各人之内。(《歌罗西书》3:11)
普世主义曾经一度凭借罗马公民权的概念得以实现,现在则体现在基督教所有信徒组成的共同体的理念里。但是由于现在承载所有人的可居世界变成了精神性的,因此圣保罗否认基督教新人将会获得任何政治或社会的新身份。步入教堂并不会改变新信徒实际的地位。在这个世界,农奴仍然是农奴,而自由人仍然享有自由。
甚至连极端体现社会差异的奴隶制,在基督教里也不会有所变化。奥古斯丁主张,奴隶制显然是对某些罪的惩罚。那些发现自己成了奴隶的基督徒可能并不很清楚自己做了什么,但是成为奴隶这件事本身,就足以证明他确实做了某些事情,没有什么可以将其改变,奴隶因此甚至不能为了试图让自己得到解放而主张拥有自然权利。
所有这些不同的种族、宗教和文化的群体,包括斯基泰人、犹太人、希腊人、蛮族和罗马人将会一起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层次更高的世界。保罗曾经是罗马优秀的公民,基督是顺从的罗马臣民。他们都不曾选择拒绝罗马的权力,也不认为自己的教义有朝一日会传到罗马之外。两人也都在教会和国家,即精神的国度和世俗的国度之间做出了明确的区分。
耶稣曾被法利赛人问及,犹太人是否要向罗马帝国交税,他们希望他会自相矛盾。耶稣要他们拿出一个罗马硬币。有人给了他一个,上面有神化的提比略的肖像。“这像和这号是谁的?”他问道。“恺撒的。”他们回答。然后他反驳道:“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马太福音》22:21)这是一个聪明的答案。它让耶稣摆脱了一个潜在的不怀好意的陷阱。但它同时也是福音书中最重要的观点之一。基督以此清楚地说明自己的王国并不属于“这世界”。他无须与恺撒发生争执,因为恺撒并没有主张在他的灵魂的国度里拥有权威。耶稣自己,或是任何说出这些话的人,完全不会想到以耶稣之名创造的宗教将会变成什么样子。当然,他也没能预测到如此简单的一句话会对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在奥古斯丁看来,真正重要的是精神的国度。基督徒终结了由希腊人开启的历史进程。由此,他们显然也改变了它。希腊和罗马的异教徒同样是具有美德的人类,但是他们却不具备精神的德性,因此尽管很多人没犯任何错,他们仍然不会得到耶稣的救赎。他们是只属于一个世界的公民。不过随着基督降世,世界不再是一个,而是两个,或者用奥古斯丁的话来说,存在着两座城市。一座是尘世之城,由该隐所建,所有人都不得不在这里过他们的生活;除此之外,还有一座“上帝之城”,也就是这世界上基督的教会及其成员。
城市(civitas)这个词可以同时表达上述两层含义。其他语言没有类似的单词可以准确地描述上帝的受膏者身上前定的合一。但是在奥古斯丁看来,至少在第二次降临消解人类全部历史之前,虽然尘世和精神世界不可避免地纠缠在一起,它们也是无可救药地相互分离的。而以罗马帝国为最佳代表的“俗世之城”,尽管最终注定要灭亡,仍有其存在的必要,否则世界就将会因为人类的原罪而充斥着无情的暴力,秩序将不复存在。和雅里斯底德充满热情的主张不同,在奥古斯丁看来,罗马帝国不会永存不灭,永恒的只有上帝之城。不过虽然它具有人类的弱点,脆弱而且转瞬即逝,但仍然是比之前更好的政治形态,只要能够保持城市赖以建立的美德,它就会继续存在下去。按照他的说法,罗马人已经得到了“俗世的光荣,他们的帝国无人可及”,这是为了奖励
他们的美德,他们选择了一条艰难的道路,最终给他们带来了这样的荣耀。他们为了公共财富,不顾个人财产。他们面对贪欲态度坚定,给自己的国家提建议时毫不动摇,不会触犯任何法律,也没有任何非法的欲望。
相比之下,上帝之城是永恒的,“没有人在那里出生,因为没有人死亡。会有这真正的幸福不是因为美德,而是因为上帝的恩泽……在那座城里,太阳不会同时照耀着‘善人和恶人’,‘公义的日头’只会给善人带来光明”。奥古斯丁只关心这两座城市所代表的价值,而不在乎它们在各自领域内的司法管辖权。不过通过对人类的内在和外在生活做出如此明确的区分(异教世界对此几乎是一无所知的),《上帝之城》在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制造了裂痕,这将会在两座城市假定的继承人——教皇和皇帝——之间激烈而漫长的斗争中得到具体体现。战争的结局是,欧洲的世俗统治者们成功地从教会手里夺回了自己领地的权力。我们将会看到,二者的对立在随后西方与另一支来自亚洲的恐怖的新力量对抗时,将会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当奥古斯丁坐下来撰写《上帝之城》时,他目睹了罗马帝国在西方覆灭的开端。他也意识到了另一种分歧,也就是上帝之城内部的分歧,只是他永远都不可能预见到它会造成怎样的后果。395年,由君士坦丁统一的罗马帝国再次分裂,而这次是永久的分裂。首都位于拜占庭的东部帝国后来被称为“拜占庭帝国”。它更加富裕,实力更强,疆域也更为广阔,而且和经常陷入无政府状态的西方相比,它存在的时间要长得多。与拜占庭帝国形成对照的是,西方将会逐渐衰落,分裂成一系列纷争不断、落后的小王国。
等到阿拉里克的哥特人出现在西罗马帝国边境的时候,君士坦丁堡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新罗马了,它是中国以西最大的城市,人口达50万,为了保障粮食供给,城市修建了1.5英里长的码头,以停靠运送谷物的船只。即使是拜占庭帝国内稍逊于君士坦丁堡的安条克和亚历山大港,此时也已经和罗马规模相当。与西方混乱拥挤的城市不同,君士坦丁堡到处是林荫大道和宽阔的广场,在罗马还未被居民住宅填满各个角落时,也曾有过这样的景象。君士坦丁堡的皇宫和罗马大多数宫殿不同,不是已经部分损毁的老旧建筑,而是恢宏的新建筑,有拱顶和廊柱,里面有花园和喷泉。城里的居民和城市的建筑一样雍容华贵。“希腊人有的是黄金和宝石,”稍后到来的一位阿拉伯访客用明显惊叹的语气写道,“他们的衣服用丝绸制成,金丝玉刺绣镶边。看他们穿的衣服和骑的马,人们一定觉得他们都是王子。”
这样,东部帝国的文化不可避免地与同一时间拉丁西方缓慢出现的文化越来越不同。虽然在1453年败于奥斯曼土耳其人之前,拜占庭帝国总是将自己视为罗马帝国,而其臣民也自认为是罗马人,但是希腊语在它的宫廷和宗教用语中占比越来越高(不过法律用语仍然以拉丁语为主),整个社会也变得越来越希腊化。拜占庭的皇帝(basileus)与西方的君主截然不同,他们更接近希腊或波斯王国的祭司兼国王。结果,在皇帝身边出现了一个庞大、复杂的宫廷,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更粗俗、更简朴、更“野蛮”的西方人几乎看不出它和亚洲君主令人叹为观止的宫廷有什么区别,它们同样奢侈、华丽、精致。
不仅如此,从地理上来说,拜占庭很大一部分领土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属于亚洲的。它的东方近邻是古代晚期的另一个强权:萨珊波斯帝国。和所有的邻国一样,不管它们如何敌视对方,通过两国变化不定的边界,仍会有大量的交通往来。直到7世纪早期,东方的很多基督徒实际上居住在现在的伊拉克境内,因此需要服从萨珊帝国的“万王之王”的政治权威。在那些住在遥远的西方的拉丁人看来,希腊人和他们以前的敌人之间的共同之处,甚至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以外的“野蛮的”同信仰者要多得多。在现代语言中,“拜占庭”这个词并不偏重于特指属于拜占庭的某物或某人,它更多的是指难解的、扭曲的、过于复杂的,很可能也是虚假的事物。
东西方的基督教很快就开始产生差异。二者的不同之处甚多,其中最为显著的、在随后几个世纪里会对东西方所有文化与政治图景产生影响的是教会与国家,也就是神圣的国度和世俗的国度之间的关系。
对君士坦丁大帝来说,基督教理所当然要成为与异教以及所有形式的宗教相同的统治工具。和之前的希腊人一样,罗马人一直以来也很清楚这一点。不管他们自己对神的实际看法如何,不论他们的信仰是真是假,虔诚既是宗教责任,也是政治义务,这就是为什么维吉尔将罗马英雄奠基者埃涅阿斯形容为“英勇无双、虔诚无比”。早期的罗马基督教国家认为没有任何理由要改变这一点。异教的皇帝本身就是神,尽管他们不得不等到死后才会获得正式的封号。他们的统治权和罗马元老院曾经拥有的不同,并不是单纯的世俗权力,而是由他们所独享的半神秘的权力,只是不管是君士坦丁,还是他的继承者,都无法宣称自己是这样的神(尽管主教们不得不经常提醒他们这一点)。不过即使他们从来都不是不朽的,他们也已经超出了单纯的人的范畴。即便他们无法将自己封为神,他们仍可以做到仅次于此的事:使自己成为神在大地上的代表。
异教的皇帝们总是保有“大祭司(Pontifex Maximus)”的头衔,甚至连君士坦丁也继承了这个名号。在基督教取得最终胜利之后,这个头衔也被废弃了,不过拜占庭的皇帝继续视自己为可居世界的统治者,而且也得到了教会的承认,只不过可居世界这个词现在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同义词,皇帝也因此成了上帝在现世的总督。皇帝由自己挑选的牧首为自己加冕。和其他人不同,他可以进入圣堂。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之前,基督教世界的其他人在圣餐礼中只能分领基督的身体,而皇帝则可以同时分领基督的身体和血(和被桉立的牧师一样,不过他并不是牧师)。在某些特定的节日上,他会在圣智大教堂,也就是圣索菲亚大教堂布道。正如神在地球上有自己的宫殿,皇帝亦如此。在438年狄奥多西二世颁布的《狄奥多西法典》中,整个皇宫,包括皇帝的马厩,都被宣布是神圣的。皇帝也成了法律唯一的来源。按照查士丁尼充满敬意的说法,他是“不受束缚的立法者”,法律总是体现了他“直白的良好意愿”。法律既是国家事务,也是宗教事务。
这并不意味着在教会和国家、牧首和皇帝之间不存在紧张关系。和西方一样,拜占庭的教会保持着独立。也因为教会解释上帝的律法,以上帝的名义介入俗世,因此和西方一样,绝大多数神职人员认为教会的权威只能在国家的权威之上。“皇帝的权力是一回事,”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直言不讳地说道,“教会的权力是另一回事;后者高于前者。”至少在理论上,拜占庭是由双重权威统治的,这经常被比作人由灵魂和身体两部分组成。皇帝选择牧首,但是牧首可以在加冕前要求皇帝保证信奉正统教义,他们也确实是这么做的。牧首也可以绝罚皇帝。906年,利奥六世被逐出教会;1262年,米哈伊尔·帕列奥列格同样被逐出教会。但是即使如此,在拜占庭,恺撒的王国和基督的王国的关系比在西方更加和谐。直到帝国迎来自己悲惨的结局之前,教会一直维持着自身的独立和对信徒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