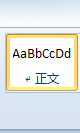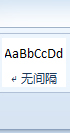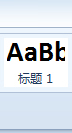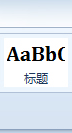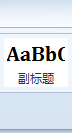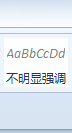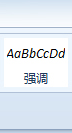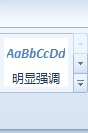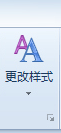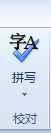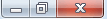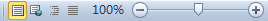到%确定
订婚典礼
我与钱锺书是志同道合的夫妻。我们当初正是因为两人都酷爱文学、痴迷读书而互相吸引走到一起的。
——杨绛
情到深处,就想与之永远在一起,无论沧海桑田。
钱锺书从清华毕业后,迫切想要与杨绛结婚。他们两人虽是自由恋爱,但该遵循的习俗一样也没少。媒妁之言、订婚典礼都是必经环节,虽有封建的一面,却也有仪式感的美好。
钱锺书知道杨荫杭对自己印象还不错,没有同杨绛商量,便同自己的父亲钱基博去苏州拜访未来的岳父。父子二人上门求亲,邀请了两家都认识的友人作为媒人。
本来,两家都是无锡人,也陌生不到哪里去。钱基博和杨荫杭虽是初见,却早已听说过对方的大名,两人从古代文学到近代文学,从法律到政治,聊得不亦乐乎。等到想起钱家父子是上门求亲来的,杨荫杭以为杨绛知情,他一向开明,当然尊重女儿的想法,就同意了。杨绛虽然事先不知道,但内心一定是愿意的,喜欢的男孩上门求亲,是他对自己的情意做出的最诚挚的表达。
钱家父子上门求亲不久后,两家便决定举办订婚典礼。
因为杨荫杭身体不太好,所以决定一切事宜从简。订婚典礼在苏州一家饭馆举行,两家人的亲朋好友欢聚一堂,高谈畅饮,共同祝福眼前的一对小儿女。杨荫杭因着喜事,一扫病体的不适,精神焕发。杨绛的母亲也同亲家母聊着家常,大方得体。钱锺书后来告诉杨绛,自己的母亲回家后,高兴得一晚上睡不着觉。儿女的喜事,给双方家人带来了很多快乐。钱穆先生也参加了他们的订婚宴席,他当时在燕京大学任国文讲师。宴席结束后,钱基博把杨绛介绍给钱穆先生,请他多多照顾。
钱基博对这个未来的儿媳特别满意。原来老先生在儿子不知情的情形下,偷偷地拆看了多封杨绛寄给钱锺书的信,其中一封信,杨绛写道:“现在吾两人快活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终不受障碍。”钱基博看了之后,摸着胡须,十分受用,他称赞杨绛:“此诚聪明人语。”那时,钱基博就已经认准了杨绛这个儿媳,他十分欣赏这个女孩的聪慧与识大体,不似别的有钱人家娇滴滴的小姐那般以自我为中心。他觉得,“痴气”的儿子终于有人可以托付了。
订婚后,杨绛多了一个称呼:钱锺书的未婚妻。
钱锺书从清华毕业后,婉拒了师长让他继续攻读研究生的建议,接受了上海光华大学的聘书,任英文系讲师。父亲钱基博也在光华教国文,父子同在一所大学教课。
杨绛即将北上,钱锺书送她到火车站,钱穆先生也已到达。他们一起办理好行李托运,登上火车。杨绛和钱锺书还沉浸在订婚的喜悦中,却又不得不再次分离,相思的苦楚袭来。不过这次是甜蜜的相思,他们十分确定对方就是陪伴自己一生的人。道别的月台上,他们挥手惜别,北上的列车缓缓驶走。
那个时代,从苏州到北平,火车要走三十多个小时。在南京换乘北段火车时,钱穆先生对杨绛说:“我看你是个有决断的人。”杨绛很惊奇,钱先生又说,“只看你行李简单,可见你能抉择。”杨绛便在心里偷笑。上次她去清华借读,带了很多大箱子和铺盖,全没用上。这次她当然长经验了,但她只是谦虚了几句,并没多说。
火车轰隆隆地行驶着,窗外的风景不停变换,从水汽氤氲的江南慢慢过渡到江北景色。杨绛和钱穆先生不太熟悉,话也不多。他们各自吃着所带食物,杨绛吃的是饼干和水果,请钱穆先生共用,先生却拒绝了。先生在车上吃的是麻片糕点心,等到停车,就去月台喝一碗油豆腐汤。虽然已工作多年,但钱穆先生依然很俭朴,杨绛对他更加尊重。
过了蚌埠,窗外的景色一片荒凉,周围全是土墩子。杨绛忍不住叹息这段路太过乏味,钱穆先生却解释:“此古战场也。”他指点杨绛,哪里可以扎营,哪里可以冲杀。杨绛的眼前便浮现出《吊古战场文》的场景,自己仿佛回到了古时的战场,一个个土墩子化作了冲杀的千军万马,肃杀之情顿生。等到靠近泰山时,钱穆先生又给杨绛讲述临城大劫案的事件,以及抱犊山的典故。
这段旅程因为有了钱穆先生的讲解,从枯燥变得有趣。杨绛十分钦佩钱穆先生的才学,但那次分别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两人曾经路过古战场,大概没有预料到自己的家国不久后也会硝烟四起。兵荒马乱的岁月,谁又能知道,哪一次相见是最后的相见呢?
清华还是那个清华,却多了新的女生宿舍楼,名“静斋”。
杨绛挑选了三楼边上向北的小屋,视野开阔,透过窗子,可以看到苍茫的西山,还有一些乡村野景。谁承想,到了冬天,这间屋子的弊端就显现出来。凛冽的北风,呼呼地从窗户的缝隙吹进屋子,还夹杂着很多沙尘,吹得屋里到处都是。杨绛只好搬进了高年级同学赵萝蕤的房间。赵萝蕤是叶公超先生的学生,研究的是英国诗人艾略特,后来成为著名的翻译家,翻译了艾略特的《荒原》。
赵萝蕤曾经是燕京大学的校花,追求她的人非常多。有一次,她问杨绛:“一个女孩被一个男孩爱,是否足够?”不知当时杨绛是怎样回答的。赵萝蕤后来选择了家境贫寒的同学陈梦家做丈夫,那又是另外一个感人的爱情故事了。
心仪的学校和心仪的专业,让杨绛很满意。她一口气选修了很多名师课程,包括翟孟生先生的欧洲文学史、梁宗岱先生的法国文学、吴宓的中西诗比较以及朱自清先生的散文。她觉得自己是跨专业学生,底子薄,便格外用功。有一次,梁宗岱先生提问她,她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出错了,没想到梁先生是在夸她,此后她也渐渐有了自信。
在朱自清先生的散文课堂上,她交了一篇习作——《收脚印》,描写人死后灵魂到生前去过的地方收脚印。这篇文章用词清丽,又带着淡淡的惆怅和伤感,朱先生看了后,很是赞赏,拿去投稿。不久,这篇文章就刊登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稿费五元钱。杨绛很开心,她花四元钱买了绛红色毛线并织成一条围巾,剩下的钱买了天津起士林咖啡糖,和围巾一起寄给家中的妈妈。
每当放假,杨绛回苏州,钱锺书都会去探望她和她的父母。不见面时,他们仍旧像在清华读书时,每天坚持通信。无锡和苏州之间的书信来往,没有南北通信那么慢。他们的信已不复初相识时只论学问,信中有很多诗作,寄托着两人的情思。
后来,钱锺书把信中作的诗与杨绛的唱和诗自费出版,编成《中书君诗》,赠送给要好的朋友和师长品评。吴宓先生读完后,称赞他“才情学识谁兼具,新旧中西子竟通”。有的学者只研究国学,对西方文学并不精通;有的学者只喜欢西方文学,对中古文学并不赞赏。而钱锺书是少有的精通国学和西方文学,并能把古今中外文学融会贯通的学者。这个特点,从他年少时的诗歌和杂文就可看出。
契合的爱情,是求学路上最好的催化剂。钱锺书和杨绛两人琴瑟相和的爱情,激励着他们在治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